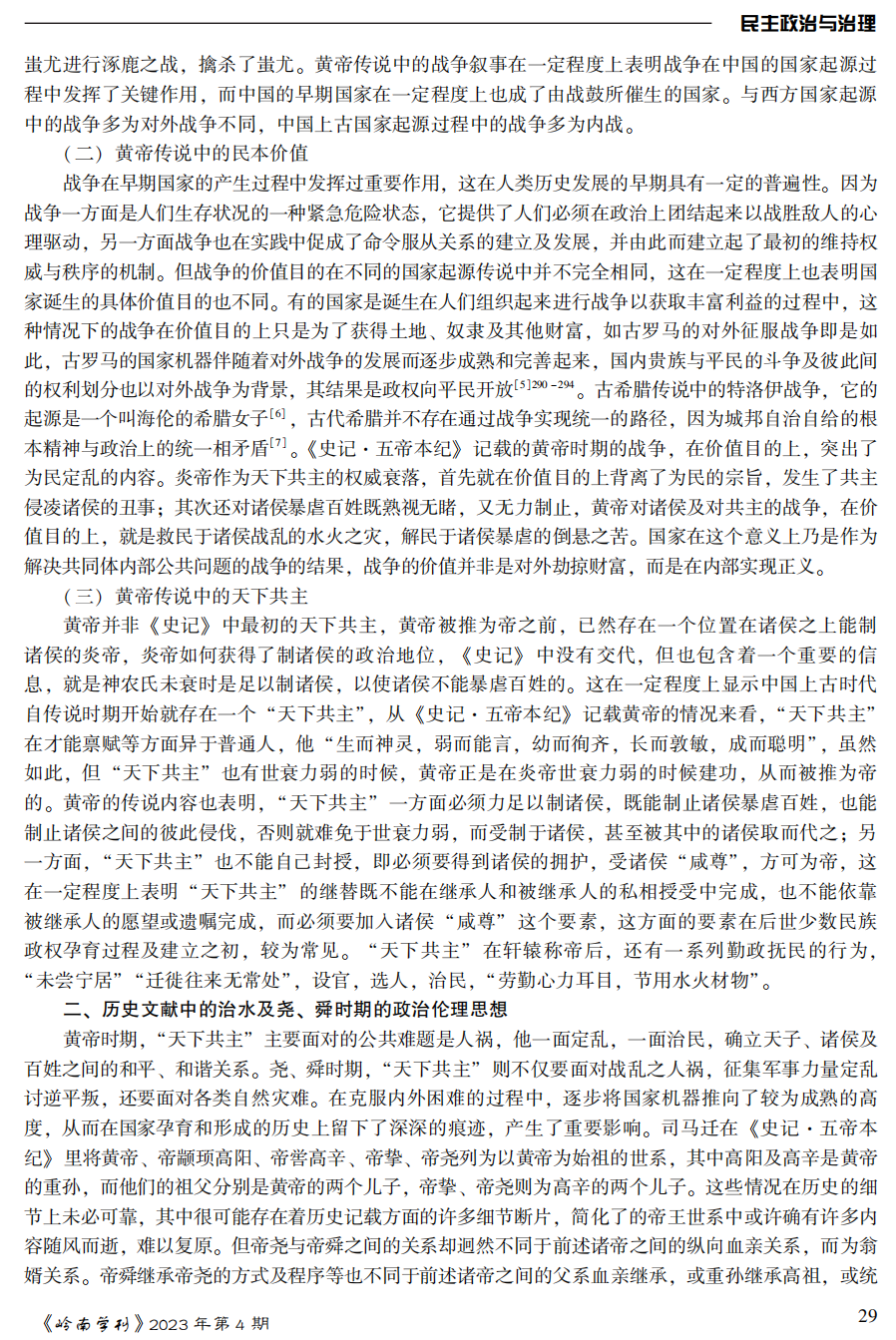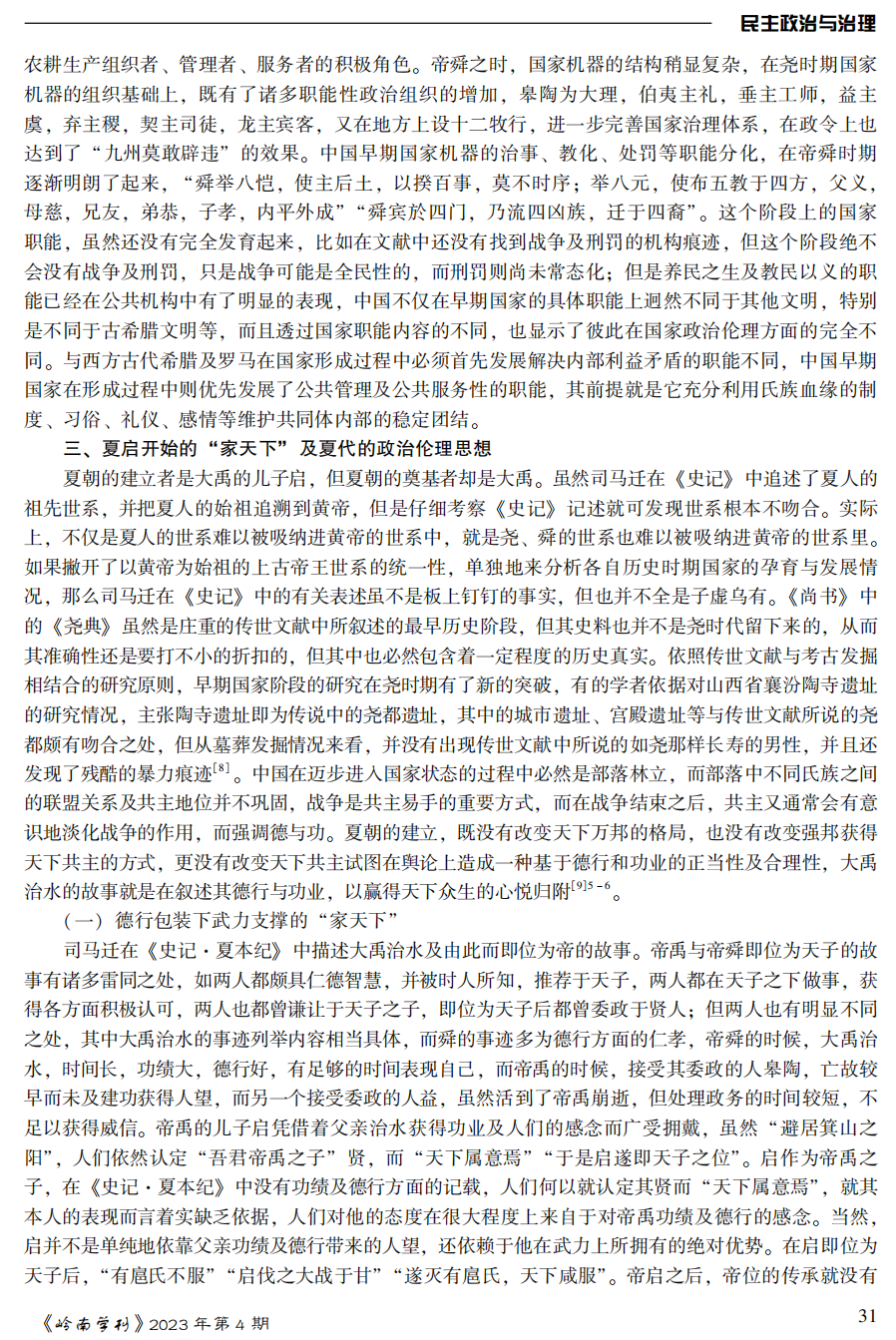张师伟,薄萧.从传说到历史:中国上古国家诞生进程中政治伦理观念的阶段性发展[J].岭南学刊,2023,(4):27-32.
从传说到历史:中国上古国家诞生进程中政治伦理观念的阶段性发展
摘要:中国上古传说的源头无疑是神话传说,但传说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历史化的重大转变,传说的内容被归纳进了历史叙事的脉络中,并展现了其伦理化的内容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为国家出现准备伦理论说的端倪。这种端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发育的实践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发育的要求,虽然它主要是通过故事性叙述而非通过言论来表达其内容,但它已经在事实上开启了中国政治伦理思想从传说中走出来的思想行程。当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表达逐渐达到了可以用语言做清晰表达的时候,它就走完了从传说到历史的历史行程与理论进程,初步具备了政治伦理思想的架构雏形,并具备了同国家机构进行互动的自觉性。中国政治伦理思想一旦发育到了这一程度,历史也就由此而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家天下的阶段。
中国上古时期的早期国家因为缺乏可靠充分的材料,所以并不能在时间上有一个准确的起点,但在国家机器达到成熟阶段之前肯定存在一个早期国家的阶段,而早期国家在政治伦理观念上的成果也必定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孕育、发展过程才获得的。它在内容上与国家诞生过程中政治观念的发展具有时间及内容上的连续性,在一定意义上,恰好是国家形成过程中在政治伦理观念上的积累性发展,造成了一种可以支持成熟国家机器的政治伦理观念基础,从而为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巩固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伦理观念基础。早期国家就其定义而言乃是指国家形成的早期或初期阶段,基本上可以说它是国家初生时期的样态,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发展的最简单状态,即作为一个国家,它在形态上获得了最简单的结构及功能的完整性,比这更早的时期,国家在结构上或功能上还不完整,比这晚一些时期,国家则已经超越了它的最简单状态而有些许复杂了。作为国家的最初亦即最简单的状态,不同地域及文明传统的人们当然创造了不同具体形态的早期国家组织,但作为早期国家,不同地域及文明传统的早期国家之间又存在着起码的共性。“早期国家都是从史前氏族部落或其他某种较小的人们共同体演化而来”,它的“类型,如果不算酋邦,成文史载的早期国家可以说都是君主国”。当然,这并不是说各个地方的早期国家都会存在共同的国家标志,实际上,考古学界明确提出了国家出现在考古学上的共同标志,如以城市、文字、礼器、铜器等作为国家出现的标志,但也有学者对这种所谓的标志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因为中国史籍中保存的北方民族国家如匈奴等显然缺乏考古学意义上的标志,但就史籍所载而言又很难否定匈奴早已进入国家阶段;所以考古学界所谓国家出现的标志也只能仅供参考,而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国家是否存在的标准依据。中国的国家在有成熟文字记载的史料之初,就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形态,它在缺乏较为成熟文字史料记载的阶段,就大致可以作为它的早期阶段,能够作为这个阶段国家存在之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可靠的历史文献,而依靠历史传说史料来表现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阶段则归入了国家形成时期。中国的国家形成在传说内容上比较丰富,能够覆盖从人工取火至早期国家形成的漫长时期,但是从早期国家诞生所需要的直接要素的凝聚来看,又不需要追溯太过久远的传说内容,而仍主要聚焦于被历史文献记载的据说是可以当信史看待的历史传说,因为它在早期国家形态及相应政治伦理观念上的影响力更为直接,也更为明显。虽然不同的早期国家在形态及结构、功能等方面还比较简单,但已经各自获得了形态不同、结构各异及功能不尽相同的完整性及个性等,彼此之间在政治伦理上的差异,已经在观念、制度及行为等方面稳定地呈现了出来,并由此而奠定了各自在以后历史进程中的方向、框架、结构及功能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可不察。值得注意的是,各个早期国家在形态、结构、功能及其政治伦理观念上的不同,都可以从历史传说中梳理出发展的头绪,并找到它的源头。中国上古的国家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和准备时期,在从氏族及部落到国家的渐变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神话故事,比较完整地叙述了从开天辟地到国家诞生的故事情节。虽然许多的故事情节都带有明显的神话色泽,显得荒诞,但在荒诞的内容当中也不能排除其中可能包含的部分历史真实,即在中国大地上人类从原始群时期到国家诞生的整个过程中,每一步有历史意义的跨越性发展都与杰出的英雄人物有关。从开天辟地的盘古、抟土造人的女娲,到改善了人类生存条件的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有关的神话故事记录了中国大地上的史前人类在征服、改造和利用自然等方面的不平凡履历。这个阶段所产生的神话故事,虽然没有突出中国史前社会的人们在社会及政治领域的创造,但在思维方式上已经彰显了历史主义、世俗主义、人本主义的特征,即人类在征服、改造和利用自然方面所留下的历史痕迹,并没有如同古代希腊及希伯来那样突出了诸神的地位和作用,而是突出了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了人类创造性的重要性,彰显了人类力量在历史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国大地上的国家孕育发生了划时代的重大变化,留下了较为丰富的国家孕育事迹,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开始在实践中得到了最初的展示。黄帝的传说由来已久,虽然古史辨派以黄帝事迹在史籍中晚出为由,怀疑黄帝作为古史人物的可靠性,因为战国中后期以后,对黄帝的崇拜才逐渐流行,并成为华夏一统的标志。这固然不能排除黄帝传说的推广者确有托古言志的政治动机,但该传说的形成也绝非凭空产生,必然有相当丰富的传之久远的古史故事依据。司马迁的《史记》在叙事上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也以黄帝故事有一定的历史可靠性为前提。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黄帝的故事首先聚焦于激烈的战争。首先,黄帝时期的政治世界面对着神农氏衰落而造成的战乱,“诸侯相侵伐”“神农氏弗能征”,权威陨落,战乱频仍,诸侯彼此侵伐而又势均力敌,战乱所形成的不安全,完全不可能经由法律的调节而结束,必须要以强有力的暴力来结束,国家机器的孕育就在暴力的角逐中进行着。其次,黄帝以强大的力量,他“习用干戈,以征不享”,以战争的胜利结束诸侯间的侵伐,达到“诸侯咸来宾从”的结果,确立了自己在诸侯间的权威,并进一步以强力与炎帝进行了阪泉之战,以争夺诸侯及民众的认同归属,与蚩尤进行涿鹿之战,擒杀了蚩尤。黄帝传说中的战争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战争在中国的国家起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中国的早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由战鼓所催生的国家。与西方国家起源中的战争多为对外战争不同,中国上古国家起源过程中的战争多为内战。战争在早期国家的产生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为战争一方面是人们生存状况的一种紧急危险状态,它提供了人们必须在政治上团结起来以战胜敌人的心理驱动,另一方面战争也在实践中促成了命令服从关系的建立及发展,并由此而建立起了最初的维持权威与秩序的机制。但战争的价值目的在不同的国家起源传说中并不完全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国家诞生的具体价值目的也不同。有的国家是诞生在人们组织起来进行战争以获取丰富利益的过程中,这种情况下的战争在价值目的上只是为了获得土地、奴隶及其他财富,如古罗马的对外征服战争即是如此,古罗马的国家机器伴随着对外战争的发展而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国内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及彼此间的权利划分也以对外战争为背景,其结果是政权向平民开放。古希腊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它的起源是一个叫海伦的希腊女子,古代希腊并不存在通过战争实现统一的路径,因为城邦自治自给的根本精神与政治上的统一相矛盾。《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时期的战争,在价值目的上,突出了为民定乱的内容。炎帝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衰落,首先就在价值目的上背离了为民的宗旨,发生了共主侵凌诸侯的丑事;其次还对诸侯暴虐百姓既熟视无睹,又无力制止,黄帝对诸侯及对共主的战争,在价值目的上,就是救民于诸侯战乱的水火之灾,解民于诸侯暴虐的倒悬之苦。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乃是作为解决共同体内部公共问题的战争的结果,战争的价值并非是对外劫掠财富,而是在内部实现正义。黄帝并非《史记》中最初的天下共主,黄帝被推为帝之前,已然存在一个位置在诸侯之上能制诸侯的炎帝,炎帝如何获得了制诸侯的政治地位,《史记》中没有交代,但也包含着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农氏未衰时是足以制诸侯,以使诸侯不能暴虐百姓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上古时代自传说时期开始就存在一个“天下共主”,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的情况来看,“天下共主”在才能禀赋等方面异于普通人,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虽然如此,但“天下共主”也有世衰力弱的时候,黄帝正是在炎帝世衰力弱的时候建功,从而被推为帝的。黄帝的传说内容也表明,“天下共主”一方面必须力足以制诸侯,既能制止诸侯暴虐百姓,也能制止诸侯之间的彼此侵伐,否则就难免于世衰力弱,而受制于诸侯,甚至被其中的诸侯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天下共主”也不能自己封授,即必须要得到诸侯的拥护,受诸侯“咸尊”,方可为帝,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天下共主”的继替既不能在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私相授受中完成,也不能依靠被继承人的愿望或遗嘱完成,而必须要加入诸侯“咸尊”这个要素,这方面的要素在后世少数民族政权孕育过程及建立之初,较为常见。“天下共主”在轩辕称帝后,还有一系列勤政抚民的行为,“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设官,选人,治民,“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黄帝时期,“天下共主”主要面对的公共难题是人祸,他一面定乱,一面治民,确立天子、诸侯及百姓之间的和平、和谐关系。尧、舜时期,“天下共主”则不仅要面对战乱之人祸,征集军事力量定乱讨逆平叛,还要面对各类自然灾难。在克服内外困难的过程中,逐步将国家机器推向了较为成熟的高度,从而在国家孕育和形成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产生了重要影响。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里将黄帝、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挚、帝尧列为以黄帝为始祖的世系,其中高阳及高辛是黄帝的重孙,而他们的祖父分别是黄帝的两个儿子,帝挚、帝尧则为高辛的两个儿子。这些情况在历史的细节上未必可靠,其中很可能存在着历史记载方面的许多细节断片,简化了的帝王世系中或许确有许多内容随风而逝,难以复原。但帝尧与帝舜之间的关系却迥然不同于前述诸帝之间的纵向血亲关系,而为翁婿关系。帝舜继承帝尧的方式及程序等也不同于前述诸帝之间的父系血亲继承,或重孙继承高祖,或统一高祖的平辈之间的继承,或父死子继,或在兄弟间择善而立,依照《史记》的记载,帝舜继承帝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上古时期的禅让。事实上,禅让并非仅限于尧、舜、禹之间,而应该在中国上古时期国家发育的一定阶段上普遍存在着,尧舜故事提供了禅让制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帝尧名放勋,作为帝喾高辛的儿子,并非初始的帝位继承人,他所以能被立为帝尧,就是因为帝挚作为帝喾继承者,表现不善。放勋仁智双全,“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人品精贵,“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注重修德,“能明驯德”,能睦九族,章百姓,和万国。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虽然追述了舜的血缘世系,并将其始祖也同样追述到了黄帝,作为帝颛顼的后裔,在颛顼之后即为庶人,舜所以被尧选中,几乎完全出自于他的善。舜之善首先在于他的孝友,虽然父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但舜仍“顺事父及後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舜顺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年二十以孝闻”。舜之善,既能在父亲需要的时候,顺事之,小过受罚,也能在父亲欲杀自己时能成功避逃,“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舜之善,其次还表现在他能有效感化人,具有引导他人向善的强劲影响力。“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又“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舜成了一个具有道德吸引力的善人,“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即位之前如何善,记载缺失,无从考问,而舜即位之前的善却在《史记》中有远比尧之善有更多的故事叙事,虽然故事的叙事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但至少表明故事叙事之中的善的内容支撑了舜即位做天子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国家治理的根本在任贤,而任贤的根本即在于贤君,贤君之贤不仅在自贤,更在于任用贤人。在《史记·五帝本纪》的尧舜叙事中,任用贤人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任贤的首要前提就是知人,尧在任贤方面颇有知人之明,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大臣举荐可用的贤人,并找出了所荐之人的不可任事之原由。面对着“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急于寻找能善治洪水的贤人,要求四岳举荐人选,但是仍能清晰地判断出被四岳举荐的鲧的不足,并认为鲧的性格气质决定了其不可用。尧曰:“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从四岳而用鲧治水,历经九年,功不成。尧之用舜,也开始于他要求四岳等“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中的贤人,并在实践中考察其贤的真实性,“尧妻之二女,观其德於二女”“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舜“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於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考察结果是“尧以为圣”,并以舜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即位为天子。舜任用贤人也是十分突出的,比如他任用诸位贤达为大臣,“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穀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中国上古时期的社会组织及农耕生产特征对国家职能的内容要求,在尧、舜时期得到了较好的满足。尧、舜时期,国家还在形成的过程中,但已经非常明确地突出了“德”的要素,这一方面体现为“德”方面的瑕疵会成为即位为天子的障碍,如舜如果“德”不是非常突出,不仅根本不可能获得四岳的认可与推荐,而且也根本过不了尧设下的检验,从而无缘于天下共主的天子之位,另一方面表现为“德”方面的不足会失去人们的拥戴,就如尧之兄弟挚,即便即位,也会被废黜而另选有德者。《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尧之时,国家机器的结构还比较简单,但也颇为重视事关农业农时的历法,“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作为一个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历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的这个职能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国家作为农耕生产组织者、管理者、服务者的积极角色。帝舜之时,国家机器的结构稍显复杂,在尧时期国家机器的组织基础上,既有了诸多职能性政治组织的增加,皋陶为大理,伯夷主礼,垂主工师,益主虞,弃主稷,契主司徒,龙主宾客,又在地方上设十二牧行,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在政令上也达到了“九州莫敢辟违”的效果。中国早期国家机器的治事、教化、处罚等职能分化,在帝舜时期逐渐明朗了起来,“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舜宾於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这个阶段上的国家职能,虽然还没有完全发育起来,比如在文献中还没有找到战争及刑罚的机构痕迹,但这个阶段绝不会没有战争及刑罚,只是战争可能是全民性的,而刑罚则尚未常态化;但是养民之生及教民以义的职能已经在公共机构中有了明显的表现,中国不仅在早期国家的具体职能上迥然不同于其他文明,特别是不同于古希腊文明等,而且透过国家职能内容的不同,也显示了彼此在国家政治伦理方面的完全不同。与西方古代希腊及罗马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必须首先发展解决内部利益矛盾的职能不同,中国早期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则优先发展了公共管理及公共服务性的职能,其前提就是它充分利用氏族血缘的制度、习俗、礼仪、感情等维护共同体内部的稳定团结。夏朝的建立者是大禹的儿子启,但夏朝的奠基者却是大禹。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追述了夏人的祖先世系,并把夏人的始祖追溯到黄帝,但是仔细考察《史记》记述就可发现世系根本不吻合。实际上,不仅是夏人的世系难以被吸纳进黄帝的世系中,就是尧、舜的世系也难以被吸纳进黄帝的世系里。如果撇开了以黄帝为始祖的上古帝王世系的统一性,单独地来分析各自历史时期国家的孕育与发展情况,那么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有关表述虽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也并不全是子虚乌有。《尚书》中的《尧典》虽然是庄重的传世文献中所叙述的最早历史阶段,但其史料也并不是尧时代留下来的,从而其准确性还是要打不小的折扣的,但其中也必然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历史真实。依照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相结合的研究原则,早期国家阶段的研究在尧时期有了新的突破,有的学者依据对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的研究情况,主张陶寺遗址即为传说中的尧都遗址,其中的城市遗址、宫殿遗址等与传世文献所说的尧都颇有吻合之处,但从墓葬发掘情况来看,并没有出现传世文献中所说的如尧那样长寿的男性,并且还发现了残酷的暴力痕迹。中国在迈步进入国家状态的过程中必然是部落林立,而部落中不同氏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及共主地位并不巩固,战争是共主易手的重要方式,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共主又通常会有意识地淡化战争的作用,而强调德与功。夏朝的建立,既没有改变天下万邦的格局,也没有改变强邦获得天下共主的方式,更没有改变天下共主试图在舆论上造成一种基于德行和功业的正当性及合理性,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在叙述其德行与功业,以赢得天下众生的心悦归附。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描述大禹治水及由此而即位为帝的故事。帝禹与帝舜即位为天子的故事有诸多雷同之处,如两人都颇具仁德智慧,并被时人所知,推荐于天子,两人都在天子之下做事,获得各方面积极认可,两人也都曾谦让于天子之子,即位为天子后都曾委政于贤人;但两人也有明显不同之处,其中大禹治水的事迹列举内容相当具体,而舜的事迹多为德行方面的仁孝,帝舜的时候,大禹治水,时间长,功绩大,德行好,有足够的时间表现自己,而帝禹的时候,接受其委政的人皋陶,亡故较早而未及建功获得人望,而另一个接受委政的人益,虽然活到了帝禹崩逝,但处理政务的时间较短,不足以获得威信。帝禹的儿子启凭借着父亲治水获得功业及人们的感念而广受拥戴,虽然“避居箕山之阳”,人们依然认定“吾君帝禹之子”贤,而“天下属意焉”“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启作为帝禹之子,在《史记·夏本纪》中没有功绩及德行方面的记载,人们何以就认定其贤而“天下属意焉”,就其本人的表现而言着实缺乏依据,人们对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帝禹功绩及德行的感念。当然,启并不是单纯地依靠父亲功绩及德行带来的人望,还依赖于他在武力上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在启即位为天子后,“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服”。帝启之后,帝位的传承就没有再经过帝舜及帝禹那样的流程,直接转为“父死子继”为主的“家天下”。战争在上古时期的国家诞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自黄帝战胜炎帝及蚩尤以后,在尧、舜、禹时期,战争在国家机器孕育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特别明显,至少从《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来看是如此,特别是尧与舜的时期。帝舜时期的罚也并未将其正当性溯及于天,而只是处死了治水失败的鲧,流放了公认的“四凶”。帝舜巡幸天下,重心在民生,并最终崩于巡幸的路上,帝禹巡幸天下,重心转而在朝会诸侯,并在诸侯中以诛杀立威,似有代天处罚的意味,但是毕竟还未明朗化。帝启在面对有扈氏不服的情况下,即以战争消灭有扈氏,其用意显然在于服天下。如果帝启只是以暴力的优势消灭不服的有扈氏,那么帝启就既难以把自己与纯粹的匪寇区别开来,也难以依靠暴力消灭其他的众多不服者,军事作为流血的政治,必然要寻找合理的政治上的依据,既将不服者放在罪恶的位置上,也把自己放在正义的位置上。帝启以自己为天意的代表者,不服帝启,就是不服从天意,而不服从天意就是犯了天条,天必然要处罚犯了违反天意者,但天又不能亲自执行处罚,而只能委托代表天意的帝启来进行处罚,帝启则要以恭顺的态度来“恭行天之罚”。有扈氏与帝启之间的服从与否原本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但帝启以代天执行处罚将其转变成了天与人的关系,并确立了帝启即是天意所在,服从天意,从而服从帝启,帝启就代天行赏,不服帝启,从而不服天意,帝启就代天处罚。尧、舜、禹时期,部落联盟式的政治组合在帝启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天下共主的继替再也没有如尧、舜、禹那样地禅让过,而长期地实行了“家天下”,即使是在太康到少康之间的失国时期,有羿氏等也要延续夏的家天下,而拥立傀儡天子。所谓禅让制,并不如同后世儒家所乐道的那样融洽,而是存在着较为尖锐的斗争,有可能获得天下共主地位的继承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推荐或择取程序,但彼此之间的竞争可能越来越趋于暴力化。三代禅让的故事历来也有篡夺的说法,“舜逼尧,禹逼舜”,“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各个氏族在一起,共同克服公共危机,解决公共问题,彼此之间势均力敌,难分伯仲,既在困难面前需要合作,又在共主继承方面存在矛盾,在共主地位越来越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共主的继替出现了世袭化的趋势,但在势均力敌的氏族势力均衡情况下,世袭化的家天下难以实现,氏族首领之间竞争共主的斗争趋于激烈,陶寺遗址的发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这种争夺的军事激烈性。但在夏的氏族取得明显优势后,其他氏族在政治上的衰落就难以避免,其他氏族的氏族头人很难获得显赫的政治地位,“家天下”在君主德行及爱民之仁的支撑下,较长时期地延续了下来。但一旦君主失德,并虐民以自乐,那么他的统治就难以为继,夏的末代王即以永远的统治地位自诩,并叫嚣与太阳同在,而民众则因受虐而不堪,愤言要不惜与太阳一起消亡,“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君主虐民自乐,在实践中造成了政治上的衰竭,商氏族的开明统治者汤则以德促成了氏族在政治上的崛起,并最终灭夏,取而代之,建立了商朝。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换与创新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22XZZ010)。
作者简介:张师伟(1973-),男,山西汾阳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薄萧(1995-),女,山西忻州人,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
来源:《岭南学刊》2023年第4期、岭南学刊公众号